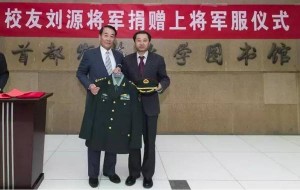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中评社12月12日消息,全国港澳研究会、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10日下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举办以“宪法忠诚与国家建构——从香港(专题)立法会宣誓事件切入”为主题的“第三十四期北大博雅公法论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在发言中表示,内地和香港在理解“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上存在差异,他指出,香港有人把除外交、国防外的所有权利都视为中央的“剩余权力”,这忽略了《基本法》是一部授权法的本质特征。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
他还表示,中央对香港回归后落实“一国两制”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预计不足,如没有及时处理去殖民化和国民教育工作,但他认为,今后仍需坚持“一国两制”,全面、准确实施“一国两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一国两制”。
香港政治事件频生 “一国两制”出问题了吗?
饶戈平表示,此次宣誓风波所折射出来的“一国两制”的问题,让很多人不禁有以下的疑惑:“一国两制”给了香港这么大的宽容和优惠,为什么香港回归以后这19年以来,我们听到的消息不是越来越好的消息,更多是坏的消息?“一国两制”到底进行的怎么样?是不是应该回过头来思考一下,“一国两制”基本法本身有什么问题?
他指出,不要把“一国两制”当成一个政治术语、政治口号来看待,而要将其视为我们国家在特定时期治国方式的一种探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种方案。“因为一国一制是常态,186个国家惟有中国搞‘一国两制’”,他认为,以宪法来保障一个主权国家实行两制的我们看不到第二个国家。因此,这对香港来说史无前例,对中国领导人也是史无前例的。
“一个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政府要管制一个资本主义的地区,一个社会主义宪法要容忍一个资本主义的存在,要让两制并存共同发展,这种面貌、这种理想能不能够实现?”饶戈平说,我们对“一国两制”本身的认识,不管对内地甚至包括中央,更不用说香港,都存在着很多认识上的差异,“特别在香港被另外诠释的一套理解,表面上都在喊‘一国两制’,喊基本法,实际上是南辕北辙的”。
“一国两制”既有理想主义 又有实用主义
他介绍,2003年“反对23条立法”的香港50万人大游行后,中央领导对“一国两制”的实施提出了“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认识,这表明我们的领导者对于“一国两制”认识的深化。他认为,这些事件提醒他们,“一国两制”远不如我们设想的理想程度,实际情况比我们想的复杂的多。
饶戈平表示,“一国两制”是我们国家处理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的政策,它从构想到国策,再到被写入法律,希望通过这种政策能达到两个方面效果:第一,在解决方式上应该符合国家最大的利益, “一国两制”首先是针对台湾(专题)问题提出来的,用和平方式来解决统一问题和领土历史遗留问题。第二,在回归后的治理方式上体现在宪法31条的规定,可以实现与国家主体不一样的制度。一国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强调国家主权的原则,强调统一的中国,强调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两制是强调两种不同的制度能够和平的存在和发展。
“让冷战时期斗了五十多年两种制度变成和平共处,邓小平说我们把国际法中的和平共处原则用在国内,这种期待和设想,是当时解决问题最现实最明智的政治选择,我觉得这个结论还是成立的”,饶戈平认为,因为这种处理是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最大化,既带有实用主义色彩,也带理想主义的色彩。
回归后治港 对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预计不足
他认为,老一辈领导人希望在他们有生之年把失地收回来,所以用这个方针收回失地,对于回归以后如何治理,他们的大致的设想就体现在《基本法》上,“你们按照我设想的、安排的往下做就行了”。但他指出,从现在看来,我们对于回归以后产生的问题预计不足,对于“一国两制”的内在矛盾、结构性矛盾,以及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是认识不足的。他举例,回归以后全国各地有很多研究港澳的机构都受命撤销、合并了,感觉香港回归了“一国两制”似乎大功告成了,香港就让它自己去管就行了,似乎看不到国家的作用,让香港自行去管理。
“香港一夜之间换了一面旗帜,他就认同这个国家了吗?”,饶戈平指出,回归后对这些问题似乎都没有做非常明晰的考虑,故他认为,在中央的工作中如何全面准确的正确认识“一国两制”也存在需要改进的方面。
“至于在香港社会这个问题更大一些”,饶戈平表示,有人说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在香港是不是太偏向强调后两句了,有些人所期待的“港人治港”似乎是一个不存在前提和基础的“港人治港”,他们讲的“高度自治”是没有限制的的“高度自治”。他认为,泛民的政治主张是希望能达成一个政治实体的完全自治,“就是他们的祖师爷英国人所教唆的”。他指出,彭定康任内搞“突击民主”深深熏陶了泛民。
误解基本法 忽略中央对特首任命权
此外,关于“一国两制”下中央的权力,饶戈平指出,香港社会有人理解,中央的权力只限于外交和国防,“剩下来”都是我们的。“有一批大律师,有一些法律学者,谈到香港和中央权力的关系的时候,甚至把联邦性的剩余权力理论运用到香港,以为基本法不加以禁止的都是我们所认可的”,而事实上《基本法》是一部授权法,用列举的方式阐明香港在哪些问题上面拥有自治权。因此,在这样的误解下,他们忽略了中央对特首的任命权。
他介绍,针对殖民时期港督是由英国委派的情况,为了体现高度自治,《基本法》规定中央不派人治理香港,允许香港领导者从本地产生。但他强调,这其中有一个中央任命的过程,所以香港特首选举是中央任命与地方选举相结合的,这个模式包括了普选的模式。“这一点被认为是违反中央的承诺,违反所谓国际标准,这个是完全媒体所宣传的结果”,他说。
而在更深层次,饶戈平分析,在香港社会和政治生态并没有因为回归而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他指出,香港社会结构、人口构成基本上是维持现状,法律制度也基本保持下来,我们没有及时进行国民教育和去殖民化教育,特区政府既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处理,因而中央在落实对香港的管治上留下了很多的漏洞。他表示,各方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之间存在差距、“一国两制”的原意与其实施情况之间也存在差距,而这种差距到最后形成了某种对立,香港社会历史上存在的“反共拒中”倾向并没有因为回归而得到根本的改变。
中央管治与地方自治 一组天然的矛盾
谈及“一国两制”深层次的矛盾,饶戈平表示,我们只看到“一国两制”我们期待的好的一面,却忽略了矛盾。他指出,香港本来就是一个缺乏国家认同的地区,甚至在英国占领香港之前,作为一个渔村的香港,对朝代的更替波澜不惊,没有什么印象。经过155年的殖民管制,香港对中国的归属感是单薄了,回归以后他们从曾经的优越感、恐惧感到现在的抗拒,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变得很突出。
“两制之间的矛盾,两制之间的差异,远不是50年可以解决的”。饶戈平说,我们当时定下“50年不变”主要是用于稳定香港人心,当时也预计2047年内地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程度,和香港的差距会减小。但他认为,从现在看,即使“一国两制”实施得顺利的话,2047年两地的差距已经减少到一种可以融合的程度还恐怕过于乐观。
饶戈平指出,中央管治和地方自治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天然的矛盾,这涉及到中央与地方权限的问题。“我们应该感谢的我们的前任,不能责怪我们的前任,更不能因为现在的误差去质疑‘一国两制’”,他认为不应动摇对“一国两制”的信念和坚持。
保证“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 中央要发挥更大作用
他表示,“一国两制”的实施更加需要中央发挥作用,“中央是‘一国两制’的制定者、主导者,也是第一责任人,尤其有必要站再一个历史的高度来认识看待‘一国两制”。他认为中央坚定不移的坚持“一国两制”,同时要全面、准确地实施,保证不走样、不变形,这个立场是很坚定的。他指出,中央应该对“一国两制”实施19年进行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总结和反思,既要充分保持香港的高度自治,新手我们的承诺,也要充分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的权利,“硬得要硬,软得要软”。
饶戈平认为,我们面对与解决的不是质疑和拷问的“一国两制”的问题,而是如何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的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一国两制”的问题。他认为,我们在这方面思想还不够解放,“‘一国两制’提出者已经过世了,对于后来的人,如何坚持这个基本国策,丰富它的构想和实践”,饶戈平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