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张艺谋拍《长城》的妥协,刘德华看在眼里,“要是我可能会发脾气,但他没有。”他也并不喜欢《长城》的海报,只是从没提起过,“没人问我我就不说。各种事上我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没人和我谈”。

张艺谋身上很多特点,都很难在现代科学体系中找到答案。他今年66岁,还是一头不符合自然规律的黑发。一天只吃一到两顿饭,睡四或五个小时,能量条却强悍到了反人类的地步。普通人的脸大多不对称,然而他大到骨骼五官,小到眼袋皱纹,两边脸几乎都能做到对应平衡,相映成趣,法令纹几乎延伸到下巴,箍出一组完整的括号——在封建迷信里倒是有说法的:法令深长过口,属吉。但是,过深、过长的话,“为人固执、自我中心、孤独”。
最难解释的,当属他的招黑体质。从他以导演身份出现在中国影坛,张艺谋就像一块磁石一样,成功吸引了各种阵营、各个角度的批评。1980年代主要是“向西方贩卖中国的愚昧和落后”,1990年代后期则是“粉饰现实”、“为政府做宣传”,2000年以来,他被看作先人一步地臣服于市场,更敏锐一点的,那时候就发现了他“商业大片背后的政治意图”。
对于学术界,张艺谋像一个不可多得的木人桩,从后殖民到后现代,从表现主义到女性主义,各种理论新招都可以用他练手。延伸到舆论,批评张艺谋就像语文教育的总结中心思想一样,生产出了一套完整而抽象的表述和语汇,比如迷恋权力、追逐名利、形式空洞、价值混乱……从作品阐释到为人,生生不息,循环不止。在嫌弃张艺谋这样的关键问题上,整个中国的文化人士,阶层不论上下,阵营无分左右,前嫌冰释,空前一致——一个人要具备怎样的磁场才能解锁上述成就,这大概也是一个无解之谜。
有趣的是,他身上确实出现过谜之遭遇。张艺谋的两任文学顾问,王斌与周晓枫,都写过他1985年拍摄《大阅兵》期间的UFO事件。当时在场共有七人,旁人都是手里搬着器材,眼里看着飞碟,嘴上议论纷纷,唯张艺谋杵在原地,出现了暂时失去记忆的“灵魂出窍”。王斌的描述里,张艺谋恢复意识的时候一车器材都已经卸完了;在周晓枫的笔下,他回神之后还来得及搬一两趟东西,看到飞碟的光束向内收敛,且能理智判断“不是飞走,而是渐渐隐没”。飞碟消失之后,原地出现了一朵“核爆炸”似的蘑菇云,还是粉红色的。
他没有记忆的几分钟里经历了什么,目前还没有一个地球人知晓。周晓枫调侃张艺谋“几近病态”的工作态度和能量,可能就是那时被外星人扫描了大脑。按照这个逻辑,他开挂似的招黑体质,莫非是扫描之后,顺手被附赠了一颗神秘芯片?
不不不,张艺谋的招黑史远早于UFO。他进北京电影学院不久,便有大字报质疑美术系扩招某学生的合理性,随后,超过报考年龄、破格录取的“摄影系的张某某”也被牵连了进来,张艺谋差一点就没法留在学校。毕业后,他和该美术系同学都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到如今,他依然是北漂,跟这个也不无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就算真的有外星人对他做了什么,那也只可能是,连他们都感受到了在这个地球生物身上,有某种无法解释的能量波动存在。
但在张艺谋那里,哪有那么多玄而虚之。“这就是性格决定的。”他干脆地对腾讯娱乐说,相比用轻巧好玩的段子一笔带过,他更愿意认真而无趣地剖析自己:“我喜欢做事,喜欢就不抱怨,哪怕做出来不被人理解,别人要从其他地方去想、去说,那我也不解释。别人怎么说你看看就完了,你知道世界就是这样的,更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见到张艺谋的时候,他只穿一件黑色短袖polo衫。虽然室内有暖气,但我们的第一反应还是:他不冷吗?
几分钟后,这种疑惑消失了。传奇影业的会议室里,讲得兴起的张艺谋挥舞着胳膊,他模仿某些批评之荒谬时,自己先笑着跌进椅子里;解释好莱坞版图之大,伸着双臂整个上身扑在桌子上。想起周晓枫曾描述,张艺谋谈剧本时总武打片似的“满场飞”:他曾绘声绘色描述自己在工厂时围追一个疯子的情景,除了表演疯子和工人,他还演迎面而来的火车——嘴里鸣笛,双臂车轮运动,“满脸都是东方红火车头的表情”。
这就是张艺谋的方式。
他把人分成两类:“干活儿的”和“谈活儿的”。“你到剧组一看就明白了,穿工装的就是干活儿的,我早期就是这样,穿个土黄色的背心,身上各种兜,像民工。穿成西装革履的,就是谈活儿的。”
早年间,他“干活儿”的样子通过各种照片深入人心:夏天大汗衫,冬天军大衣。有一张他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演员合影,所有人西装笔挺、旗袍袅娜,唯有导演笑呵呵穿着军大衣半蹲在地上,双手拢在袖子里“农民揣”。

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片段。
巩俐曾回忆有一年两人在广州火车站,她去见个朋友,让张艺谋原地看着东西,回来发现位置被一群民工占领,张艺谋却不见了。找了一圈,才发现他就在民工中间谈笑风生,“混为一体,难分彼此”。
出席重大场合也是类似形象。1988年他站在金熊奖领奖台上,深灰西装、浅蓝衬衣、鲜红领带,笑得合不拢嘴。1993年法国使馆给他颁发骑士勋章,他粉t恤、白裤子,又套了件灰西装。《张艺谋的作业》作者方希感觉,“像去相亲的乡村青年。”
“早期我是很不讲究的,品味也不高。其实到现在我都不会打领带。”他对我们解释。
但这个在我们面前的张艺谋,黑衣黑裤,自矜地不显出任何logo。方希曾仔细观察他的穿着,认为“不张扬,细看讲究”。
这使他如今看起来更像一个颇有身份的“谈活儿的”。他出席各种电影节和社会活动,有时也为别人站台宣传,每逢自己的电影上映前,还会有一段相当密集的接受采访的时间。而在他这个级别的导演里,张艺谋属于高产者,这也就意味着,每隔一两年,就会出现一大波张艺谋专访以奔涌之势攻占各大媒体——或许堪比60年一遇的饕餮?
更不用说,以他现在的知名度,都不用开口,露个面甚至具个名就已是开题。从奥运会开幕式到G20开幕式,张艺谋这三个字一定程度上已经可以代表国家形象。在越来越多的场合,我们都能见到他一身中山装的模样。侯孝贤曾在采访时颇为“友尽”地说:“我在东京看到他时,感觉他就像一个政治局的常委。”
那次侯孝贤很不客气地对《新京报》记者说:“我感觉他没有甘于做一个农民。所以他会一次次地看形势调整自己的位置,其实看他调到什么位置你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大多数不喜欢张艺谋的人都持类似评论——逻辑大体是:一个好端端的、“土生土长”的、具有深度和批判性的第五代导演,先去投诚市场,又去趋近体制,将一身才华全去零沽了现实利好,从此再拍不出合格的电影——用贾宝玉的话说,“禄蠹”。
他的形象变化成为这种自由心证中重要的论据。虽然,他其实并不是农民。“我就插了3年队,但被说了一辈子农民,这也挺好,农民也不是一个贬义词。”他对我们说。
在他看来,形象变化并不影响“干活儿的”属性,甚至很多时候,是为了更好地干活儿:“你谈广告时穿成干活儿的去谈活儿,人家不给你,说你没有艺术感觉,像工人。”
“那你有专门穿去谈活儿的衣服吗?”腾讯娱乐问他。
“基本上没有,我就是出席活动穿中山装,因为省事,不打领带,不穿衬衣,里面还穿个T恤衫,(扣子)一扣就去了,捂着就完了。就穿那么几十分钟,完了就完了。其他情况我一般还是生活装,但我知道今天有事,那就穿个黑色、规矩一点就完了。”张艺谋用了好多个“就完了”,听起来对形象输出这件事,全无耐心。
最重要的一次造型飞跃是高仓健的影响,相比身份使然、品味提升,或者省得麻烦,促成他升级的最大因素是人情。2004年两人合作《千里走单骑》,在日本做后期的时候,高仓健约张艺谋逛街,送了他三件衣服。“他其实是把店包了下来,没有其他人,衣服他也早已经挑好了。他一边装作逛的样子,一边语重心长跟我说,你可以穿这个牌子,经济上可以负担,也没有明显logo。它很舒服,不是好,是舒服、低调。”
“我马上领悟这是高仓健先生对我的批评,他觉得我瞎穿,但他也不能直说。我特别不好意思,马上把牌子记下来了,从这之后我才有了所谓的品牌意识。”张艺谋说。
作家周晓枫2006年进入张艺谋工作室任文学顾问,在她看来,相比生活中其他地方,那时的张艺谋对形象问题已经还算讲究,可能“属于公众人物的某种职业道德”——这一点我们是相信的,毕竟采访途中,工作人员敲门问张艺谋午饭吃什么,他漫不经心地摆了下手:“肉夹馍。”
在《宿命:孤独张艺谋》里,周晓枫曾详细介绍张艺谋的裤子。市面上的成品裤子对张艺谋来说“活动不自在”,专门找制装师订做了适合自己的款式:好面料、黑色、绳带、瘦腿、下端收口,裤脚可以收到靴子里。在《长城》发布会上,张艺谋穿的就是这样的裤子。
我们能理解这是一种经过设计与改良的全功能高配版工服,既满足“干活儿”的核心诉求,又体现良好品位、照顾大众审美、满足对公众人物的形象需求。但求全心切,有时候也顾此失彼,方希就曾描述:“他说话时会动不动站起来,抡开了比划、扮演,有时动作幅度太大,他习惯性要时不时把宽松的裤子往上提提,于是就能不断看到他坐下、站起、提裤子;坐下、站起、提裤子。循环往复。”
似乎也有一点像如今这个方方面面斟酌顾虑,在别人面前——也包括他自己——还是有许多毛病可挑的张艺谋。但不管怎样,成为现在的张艺谋,都已经是他对自己最好的设计。

喜欢穿黑色衣服的张艺谋。

据周晓枫书中描述,张艺谋在国外的时候得空会逛逛商场,但又补充:“张艺谋不喜欢别人说他逛店的事儿,觉得购物不是老爷们的爱好,不体面、庸俗、显得‘低级趣味’。”
果然,我们问他平时怎么挑衣服时,他说:“我就看那几个牌子、几个款式,半个小时就逛完了。”
“那你会帮别人挑衣服吗?”
“基本不帮。我只知道我要穿什么,也从来不做变化。”他继续快速终结话题。
“那戏装是你挑吗?”
“戏装当然是你定啊。因为你要讲故事,要形象思维,你当然要知道这个人物要穿什么。现实中我不太注意别人穿什么,所以到现在,我也没有拍过一个现代的、时尚的,比如什么模特的电影,如果我要拍一个那个的话,我会学习那个行业的许多东西,可能我的品位会更提高吧。”
他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实用主义:只有有用的东西,才值得他花时间与精力。
方希在书中介绍,张艺谋因为身份原因,从来就有一种“工具化”的意识:“工具化就是有用,人有了用,有些东西就不会找到你身上,你就会有空隙生存。”
在张艺谋的观点里,工具并非贬义,有用则是他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价值观。方希描述了他解释时的样子:“张艺谋忽然声音一低,脸上浮现一些笑意,‘恐怕我今天也有这个嫌疑’。”
这或许能理解,像他这个级别的“别人家导演”或务虚高蹈,或深刻批判,总能奉出个漂亮的形而上核心,张艺谋没有,他连装都懒得装一个出来:“我就是个干活儿的。”
也能理解他“谈活儿”与“干活儿”两分法中的褒贬取向:“谈活儿的永远比干活儿的容易,找毛病还不容易吗,找你没有的还不容易吗?这样不对,那样才对。但干活儿的很多时候是有苦说不出。”
事实上,张艺谋并非不善言辞,与他共事过的人都为他在业务上超强的表达能力——以及配套的体力——叹为观止并饱受折磨。但“谈活儿”还需要具备一定的kol特质,输出形象、传播理念、普渡众生。
这些从来不是他最关注的。在人生的前30年里,他全力以赴地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能干活儿的人,而后,他全力以赴地干活,以证明自己的有用。摇着扇子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轻松,从来不属于他,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带着那张严肃到苦闷的脸,在第一线身体力行地干活儿。
他其实并非天然属于“干活儿”阵营。他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医学教授,父亲兄弟仨都是黄埔军校生,再往上,他的爷爷是临潼大户,祖屋比乔家大院“只大不小”。
那有什么用。从小他就背负家庭成分的压力,成绩再好也没法入团,更不用指望上大学。他的父亲曾提出离婚,以减少“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身份对这个家庭产生的持续影响,张艺谋在被窝里装睡偷听,默默流泪。
父母没有离婚,但母亲叮嘱过张艺谋:“你和其他同学不一样,全靠你自己努力了。”
他努力“有用”,也确实因此改变了命运:一个黑五类在下乡时通过给老乡画毛主席像,迅速刷上了友好度;会打篮球让他突破出身,特招进了国棉八厂;而摄影技术又让他在工厂从车间辅助工被借调到工会做宣传工作,后来更是因此破格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而从大三开始自学导演,是张艺谋成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张艺谋的原因。
这还是取得现实成效的,更多努力未必直通“有用”,但那种“从不虚度光阴”、“正在变得有用”的感觉,一样能给他激励。在棉纺厂当辅助工的时候,他负责清理工厂地下的吸尘装置,戴三层口罩下去,出来之后只有眼白是白的。两次清理之间可以有一段休息时间,别的工人抽烟、聊天,张艺谋背诗词。“我不知道这有什么用。”他曾解释,“我就想,多学一点,艺不压身,总是好的吧。”
别人以为他一拿到相机、一出手拍片就技惊四座,他自己知道,那一张照片里,折叠的是之前3年里,他抄了几十万字的摄影书籍。而回顾电影学院那四年,他曾自夸道:“那时候的同学都挺珍惜学习的机会,很勤奋,但我可以不惭愧地说,我至少是最勤奋的之一。”
这样一个实用主义者,把自身都作为“用”的一部分——他那些为了“有用”的努力,并不是出于现实功利考虑,而是代表了他的自我价值实现。就像风雨飘摇中手边就这唯一一把桨,用久了,工具也成了意义本身。
他在人前越沉默,私下越勤奋,落差越大,展示成果就越是一鸣惊人——别人那一惊里,端的是他所有的自尊。
张艺谋上大学是破格录取,没政审、没体检、没考试,随时有走人的风险,为此极尽识相,尽力低调。而同学们很多来自电影世家,见多识广,他年纪最大,却样样需要补课:内部电影让他看得弹眼落睛,艺术影展让他否定了过去的自己,甚至北京饭店的自动门开开合合,都能让他目瞪口呆地看了一个小时——这样一个人,当初就算想走“谈活儿”道路,也得有点可谈的不是?
他唯一的证明自己的渠道,就是干活儿。以陈凯歌当年在电影学院的风头,看西安来的大龄青年张艺谋不过“貌不惊人”、“没什么动静”的印象。直到有次在摄影展上见了张艺谋的作品,“觉得此人不是等闲之辈”,生了好感,还找他谈过毕业后一起合作——而他也不是唯一这么建议的导演系同学。
这当然是重要的认可。但到今天,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做一个摄影师与导演系的同学搭班,根本不是张艺谋的抱负。陈凯歌很快也发现了,合作《黄土地》的时候,有次在黄土高原等天气拍摄,仰头看天时,陈凯歌说:“艺谋,在咱们82届153个同学中,有一点数你最强烈——心比天高。”
以张艺谋的性格,他的心气当然不可能是高谈阔论表达出来的,无非便是,同行之间见了手艺的心领神会:对方露的那一手里,下过多少功夫,又藏了多少自许。在这个角度,张艺谋对穿着打扮有多随意,对外界批评有多沉默,那也只是证明了,他对自己的手艺有多自恃——在一个实用主义者的标准里,只有那才是有用的。

张艺谋与陈凯歌。

理解了张艺谋的“干活儿论”和“有用说”,或许才能理解,为什么是他拍了《长城》,以及他为什么拍《长城》。“我相信一般导演会崩溃的。”张艺谋相当直接地对我们说。
这段时间连篇累牍的报道里,有关传奇影业CEO“在长城上打小怪兽”的心血来潮,三个编剧历经七年的创作经历,以及我们借水行船的张艺谋导演带着中国文化走进好莱坞、走向世界的勇敢尝试,已经像话本故事一样传唱。一个戏剧化的细节反复被渲染——初定导演的时候,传奇的老板问:“张艺谋?他导过这么大的片子吗?”制片人罗异答:“有啊,奥运会。”
在官方解释中,相比一部超级大片,奥运会开幕式的筹备时间更久,阵仗更大,调度更复杂——一个导演连这都能顺利完成,拍《长城》自然不成问题。
但也许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共同点:妥协。
大众观点里,妥协是最不应该与“艺术家”发生关联的一个词,无论之后对接的是什么,都会被看作是牺牲艺术自由来完成某种交换——名、利、人情,或者权力。
张艺谋的不讨人喜欢,一定程度上也有这个原因。作为一个曾经的黑五类,妥协——或者说,认命——是张艺谋的生存之道。他几乎从不采取正面对抗的方式来争取权益。电影学院在他大二时建议这个破格录取的学生结束学习的时候,他写信问家乡的朋友有没有工作机会;毕业被分配去广西,别的同学群情激愤,只有他表示“去就去吧”;至于他一言难尽的、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筹备过程中所做的妥协,有一部纪录片《张艺谋的2008》,足足用8集的体量作了记录。
“他摸索了一套在中国工作的规律,知道怎么能继续生存下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评价。
这套规律里包含妥协,但也不止妥协。他做好了回西安工作的准备,但同时也写申请给学校请求继续学习,最后被允许完成四年的学业;分配通知下发前,他争取去潇湘厂未果,到了广西厂,他和同学成立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成为同学中第一批直接掌镜的摄影师;就算在彩排前一个月,原来的开幕式方案被上级全面否决,所有人灰心丧气的时候,张艺谋一句怨言也没有,重新开始张罗新的想法,仿佛一个没脾气的泥人——最后,他更新了自己的代表作,有关2008奥运开幕式的豆瓣评分,是张艺谋所有作品中的最高分:9.5分。
“妥协和坚持,边妥协,边坚持。”张艺谋对我们解释。
这是他的“干活儿”智慧,两者缺一不可。他从来不是那种放手一搏不管不顾的人,再坏的处境,他先接受下来,再找破局的可能。相比妥协的委屈,一无所有可能才带给他更大的恐慌,不如先占上个初始分,反正可以靠自己,从1一点点经营到100——他的目标和心气始终没有变,这一点,可以有效消解妥协带来的负面情绪。
“妥协是很现实的办法,但他还不甘心,创作要维持不甘心很难。”参与奥运开幕式创意小组的陈丹青评价他。
这么多年,这个中国最著名的导演遇到的几乎只有一种玩法。像他对我们所说的,从业以来,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一个满意的剧本,“那种改一个星期就能拍的幸福的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我觉得以后也不会遇到。”他已经习惯了从一个差强人意的起点出发,东西先拿到手里,再缝缝补补——有时候我们简直要怀疑,这种缝补过程是否也构成他工作乐趣的一部分。剧本不满意,他从拍上一部作品的时候就开始修改,“第一部戏开始就是这样了”。演员不会演戏,那就让他们在镜头里看起来会演戏:一个镜头多拍几遍,总会找到他能用的3秒钟。
但到《长城》,他需要做的妥协又有不同。“每个镜头第一个说了算的不是他。”刘德华看在眼里,“要是我可能都会发脾气,但是他没有。”
电影《长城》。
中国人或许会对“张艺谋?他导过这么大的片子吗?”这类发问感到莫名其妙,但在传奇、在好莱坞,在任何一部1.5亿美元投资的大片中,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一类全球大片,在美国也就是六大能拍,商业压力很大,连续两部要是毁了,公司可能就要破产了。在他们的工业体系里,分类是细致的,流程是固定的,导演队伍也是分着行的。比如我在他们看来就不属于这行的导演,不仅我,李安同志也不属于,或者伊纳里多也不属于这一行。反而可能会选择一些广告出身的导演,年轻,好指挥,也听话,剧本打磨好了,他们把视觉上做的很炫,也挺棒的。”张艺谋说。
所以在《长城》里,虽不年轻的张艺谋也必须遵从“好指挥”、“听话”的标准:每天拍摄后,他得把素材传回美国审看;现场如果修改几句台词,得报告几个主要的负责人通过;甚至在他30年的导演经验中,第一次被要求补拍,而他也确实执行了。
剪辑权也不完全在他手上。《长城》中张涵予扮演的主帅的出殡仪式是张艺谋在修改剧本时加入的,但剪辑时差一点没有保留。于此节演唱秦腔的音乐人赵牧阳展示了一封张艺谋来信:“你在长城上的演唱,美国人本来要剪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跟他们急了,才保住。”
中国的一线导演在这样一个体系里被拿捏,不憋屈吗?
“有时候会有。”他对我们说。“我说很多导演会崩溃,就是说他的艺术个性、自我表现不能适应(这样的要求),可能就会转而成为(理解为)人跟人的关系,转而成为你对我不尊重,转而成为凭什么我得陪你们这么做,等等等等,就会扭曲。这个流程和我们原来的流程是两个流程,所以有时候会有。”
在中国导演梯队里,张艺谋已经可以算是最没有艺术家脾气的艺术家了——就像有投资人表示,张艺谋品牌容易对接资本,除了渠道之外,因为他从来没有“牛、不配合、要价高、出尔反尔”诸如此类的毛病。但毕竟,他还是为一个镜头可以从上午11点反复拍到下午6点的、为一个画面可以要求剧组从山上踩出一条路的艺术工作者,连这点创作空间都没有,他为什么还要做?
“因为你知道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是你要借水行船,是你要借人家的航道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给全世界年轻人看一个中国故事,你还要人改航道,人家不就走了。”
“先定一个小目标。”我们玩笑道。
这个长得像兵马俑一样严肃的导演并没有接这个哏,他正色道:“这可不是小目标。”
他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如他这段时间一直在反复解释的:做一个入门级产品,将简化的中国元素裹挟在爆米花电影中传播;尝试与好莱坞的“重工业”部门合作,体验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工作流程;甚至,为中国导演蹚路,“我跟电影学院的学生说,如果《长城》成功了,六大就会到你们中间来找王艺谋、李艺谋,他们是为了钱,但对你们来说,是新的可能性。”
当然,世界是多元的。有人觉得小目标,有人觉得大件事,也有人觉得,不重要。“这些都不重要。拍电影,看电影,如是而已。其他都不重要。”编剧史航对我们说。
但我们也相信,这些是张艺谋的真心话,否则,他大可以回到《归来》这样的文艺片,低成本,见功力,没有票房压力,市场与口碑的风险都更低,还能顺水推舟地为评论家们送上“张艺谋归来”——而非如今的“张艺谋已死”——之类的标题,对一个66岁的老艺术家来说,不应该是他当下的工作方向吗?
但那就不是张艺谋了。对一个实用主义者来说,文艺片与商业片“两条腿”走路的训练,工业体系的深入体验,技巧、手艺的锤炼与创新,以及,在中国与中国电影的责任感甚至使命感的驱使下的行动,对他来说才有意义,比所谓的爱惜羽毛,有用得多得多。

《长城》发布会上的张艺谋。

相比许多影评人对《长城》的批评,许多电影从业者却表达了对张艺谋的理解。连著名的以艺术为唯一指归的拖延症患者王家卫,都为一篇力挺张艺谋的尝试的微博点赞。
有趣的是,张艺谋在我们的采访中,也提到了王家卫。讲到制片人体制和导演体制的差别时,张艺谋举了个例子:“比如他(制片方)告诉你,预算不可以,这场戏必须剪掉。中国导演就不干了。中国导演在片场是皇帝:我就得这么拍,你追加预算,不够,再追加。我拍三年,王家卫哥们儿他拍五年,你管得着吗?我出来好就行,我慢工出细活啊。你还要不要我这艺术?你不就是为我这艺术来的?要不要我这感觉?那就投啊,你不投换人,让他来。完成艺术谁最大,我最大呀!——我们是这样的体系。”
我们看他绘声绘色演完,回复道:“哦,这不也挺好吗。”
他可能没想到这个反应,顿了一下:“是很好,但不是在说两个体系吗。”
那些确实都是很好很好的,只是落在张艺谋身上,他从来没有那么恣意过。
此前他采访中就表示过佩服王家卫,“我觉得王家卫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建了组打草稿,我天,大组都建起来了打草稿,拍了两个月可以不要,我就很佩服王家卫可以把一切撂到后头去,管你挣钱不挣钱,管你演员骂不骂,管你对得起对不起谁,我就是要这口。”
张艺谋恰是对立面,他一直以来颇有点自豪的,是“没亏过钱”。“早期的文艺片也没亏过啊。最早期的是计划经济,那个就不说了。计划经济的时候,咱们没有这个话题。自进入这个市场经济之后呢,大小我觉得应该都没有亏过。国内没有收回投资,再加上国外的票房,基本上不会血本无归。”他曾对媒体说。
二张纠纷时,他跟周晓枫聊到自己在新画面枉担虚名,没有实际收入,甚至没得到相应片酬,都是点到即止。周晓枫回忆:“聊了不长时间,张艺谋说不谈这个了。”但对于张伟平在外宣称实际制作费大约在一亿二、三的《金陵十三钗》投资达六亿五,张艺谋耿耿于怀,对周晓枫抱怨:“这算不算欺诈啊?六亿五?张伟平把我弄成了一个挥金如土的烧钱土财主,多招人讨厌啊!”
这可能是张艺谋最为“爱惜羽毛”的地方了:他的正当收入被人吞没,他不争取;他的电影与人生被种种诛心之论,他也不解释;唯独被说成是一个挥金如土的土财主——又不是没有经历过比这严重的污名——他倒受不了了。周晓枫描述,在《金陵十三钗》宣传期,张艺谋反常地都没有配合张伟平的口径,“即使在媒体追问下也不愿确认这个数字。”
不仅没亏过投资人,也没乱花国家的钱。奥运开幕式小组的同事们回忆他:“很有预算概念。包括指导别人怎么做,首先问会不会太贵了,花那么多钱肯定不行,不能超预算。”他自己跟厂家还价,甚至用自己跟厂家担保:体制内需要走漫长的拨款流程,而排练赶着要成品,张艺谋往往会在此时出面协商,熟练地向厂家代表作出承诺、亲切握手、签名并合影留念,像走完全套担保程序。
在这些时候,他像一个忠诚的、有效的、且深以自己的职业操守为傲的代理人。但这样的优点,放在做艺术上是否有同样效果,有待商榷。有媒体曾表示觉得《金陵十三钗》离一个特别好的作品差一口气,他回答:“那口气我非常清楚,就是一个定位,当要求电影挣钱的时候,会差那口气,就是当时一定要求这个电影挣钱。”
这很容易被理解成他一贯的向张伟平的妥协:《满城尽带黄金甲》强塞了周杰伦,《三枪拍案惊奇》启用了小沈阳,《金陵十三钗》补拍了贝尔倪妮的床戏。但二张分手,张艺谋就停止妥协了吗?那又如何解释《长城》中那一长串中国卡司?
“张艺谋跟新画面公司合作过程中,还是受到了不良影响。张伟平跟他绝少讨论艺术上的探索,总是谈哪个演员红,怎么能够增加票房。这在某种程度上,更改了张艺谋的思维方式。张艺谋以前的电影多牛啊……他不看市场的脸色,孤往绝诣,他的电影才能独特、纯粹而有力。后来,张艺谋的考量标准发生了变化,我想起他的妥协,遗憾又心痛。”写于2014年的书里,周晓枫这么解释——连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这么看他。
但张艺谋真的这么容易妥协的话,似乎很难解释他同时还在不断启用、训练新演员,其中有些甚至没有任何表演经验。更合理的解释是,他对电影类型以及相关市场有明确的考虑与预期。一个有趣的对比是,窦骁回忆在《山楂树之恋》(电视剧版 电影版)里,他一个镜头演了112遍,已经到了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说什么的境地。而《长城》中,景甜介绍自己进组第一场戏,一遍过。
这111遍的差别,显然不是演技水准上的,更大的可能是,导演对文艺片和商业片的考虑标准上的:前者可以反复琢磨到让他满意为止,后者则会根据具体的现实条件,作出一些让步。
就像他和摄影师赵小丁曾在《十面埋伏》拍摄过程中有一次矛盾,赵小丁认为等云层散去、太阳出来再拍效果更好,然而张艺谋要求直接开拍,后来他向赵小丁解释:“我们这是一个商业电影,很多明星的档期就在这几天,如果我们不抓紧拍,可能演员的时间就没有了,这不是你再多花钱多留他几天续约能解决的事。”
张艺谋认为,一个导演能拍出好作品有三个决定因素:碰到好的剧本、碰到好的演员,碰到好的自己。他觉得要做到三好很难,“有人这种时刻很多,那真的是有天才,有时候甚至是旷世之作,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但我觉得特别特别难,我们现在首先是剧本荒,第一步就要打磨很长很长时间。”
他向我们解释了第三点:“导演就是一个现场做决定的人,好的自己,就是这个状态下做的决定都是正确的,基本没有犯错误。”
在这个角度,他佩服王家卫的地方,或许是对方做决定的时候,且不论对错,受到的干扰因素更少。毕竟在他自己,很多决定上,考虑的内容超过了电影本身,比如,一遍过;比如,马上拍;比如,不能亏。
知乎上有个问题“如何评价张艺谋”,一个高票用户列举了很多片场感受与听说的细节,结论方向是:做人nice,脾气好,不发火,尊重弱势群体,等等。很显然,在这些表征中,体现是一个具体的、平易的、顾虑周详的、时常换位思考的、也就常常会被电影之外的因素干扰的好人张艺谋,但能否就推导为一个好导演,尚可两说。
“张艺谋就像是海鸥乔纳森,本来他的飞行已经可以通向自由,但不知怎么的,他突然就感受到了地心引力,根据他接受到的地心引力变化了自己的飞行轨道。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史航对我们说。
但,谁让这只海鸥对地心引力的敏感程度与顾及程度,比那只叫王家卫的强烈得多呢。毕竟,每只海鸥独创的飞行习惯,才使他们成为他们自己。

张艺谋在《金陵十三钗》中也有妥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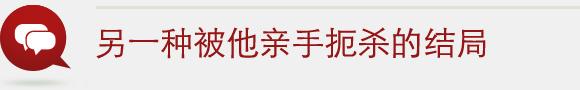
在张艺谋做过的不计其数的决定中,有一个影响至今——使他被认为是歌颂集权、迎合国家主义、主张为了大一统可以牺牲个体生命的代表,引起了大量反感,有关他电影甚至他个人的政治意图的解读就此滥觞。
对,就是《英雄》(电影版、美剧版)的结尾。秦王与刺客表达完惺惺相惜之后,大王做了决定:“杀。”蝗虫似的飞箭把刺客钉死在宫门,而大王不是不痛苦但那有什么用地流下了眼泪。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可能。在与台湾(专题)影评人焦雄屏的对谈中,他曾表示闪念要补一个镜头;在记者商羊的采访中,这个镜头甚至已经拍出来了——多了10秒钟。以我们的理解,可能前者更接近于那个习惯自我审查的张艺谋,但他描述的镜头内容是一致的:刺客被杀后,群臣内侍,或哈哈大笑,或俯首高呼:“恭喜大王,又躲过一劫!”
在这可能的另一个结尾中,刺客的舍身取义被消解,大王精于权谋计算而毫无人心,使之前的“为了更高目标之共识之牺牲”显得像个反讽。“一切都是假的,李连杰上当了。”他曾说,“如果我补了这个镜头,是不是意识形态屁股就坐正了?”
但他做出了决定,取消了那种可能。“这么做的话,梁朝伟他们的牺牲会非常可笑。”
这又是张艺谋的性格特点。他的电影当中,基本没有出现过一个“导演我最聪明”的、凌驾的反转结尾,也很少消解意义,相反,他谈戏的时候,很多时刻都需要把握一个意义核心,再出发去构建故事。
像《英雄》里的刺客无名体现的那样,“牺牲”就是张艺谋喜欢乃至信奉的命题,《长城》里他就给五军加上了这样的价值观,“让世界上一亿年轻人看到中国人不怕死,虽然打的是莫名其妙的怪兽,但中国人勇敢、信任、牺牲。”他对我们说。

《英雄》中恢弘的场面。
有一个观点说张艺谋无情,“他的骨头是冷的”,或许是没有看到他在这点上,几乎要热泪盈眶的、中二般的热爱。
他也喜欢“士为知己者死”。无名为秦王而死,他看到的背后的动机并非服膺,而是理解:“那种为了知己不顾一切的做法,那股热血(视频),那一下子使劲,那种刹那的赴死……非常震撼和感染我!这是我心中的侠义之情,就像我们看以前的黑社会电影,那些人为了自己的老大那种切指、开枪,就那一下子,很带劲——其实他们为的那个人可能是一个不值得的人,或就是一个坏人,但那个结果不重要,重要的就是那股劲!使那股劲的过程!非常动人!”他曾对记者说。
这可能导致了,《长城》没有像一个典型的好莱坞大片那样,西方男性得到了东方女性的爱慕和身体。原来的结尾是“庸俗的滚床单”,张艺谋坚持改成了现在的“战士的惺惺相惜、英雄的心心相印”。是否脱离了庸俗不好说,但是,至少,很张艺谋。
在这个角度,张艺谋如此在意“没亏过钱”、在意“挥金如土土财主”,关注点未必是钱。他在乎的是,“你既信我,我不负你”。
这是张艺谋向往的美学、价值观与相处之道。他回忆高仓健的时候,关键词就是“士之徳操”:“默默为你奉献,默默承受,不让你知道,这就是‘士’。”而高仓健又特别欣赏他:“很想有张艺谋这样的儿子。”
这大概是两个同样沉默而深情的人的相互理解。曾有媒体报道张艺谋如何与家人疏远,令老母在西安独居,周晓枫问张艺谋为何不解释——她都曾陪张艺谋母亲在北京看戏。张艺谋举了高仓健的例子:高仓健没有出席母亲的追悼会,导致媒体一派批评,但守墓人却发现高仓健在墓园守了一晚。在云南拍《千里走单骑》时,高仓健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每天有一束鲜花送到房间——后来他发现高仓健随身带着母亲的照片,以鲜花供奉。
《千里走单骑》是张艺谋为高仓健度身打造的剧本,高仓健剧中名字高田刚一,就是原名小田刚一和艺名的变体。人物是个极其沉默的父亲,一个人生活,独自看海,对家人一言不发——画外音之外,人物第一次开口,得到他来到另一个国度以后了。在中国,他看到有人想念儿子当场大哭:“我非常羡慕,能够肆无忌惮地大哭,在别人面前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是高仓健的台词,何尝不是张艺谋的内心。
他们都极其重视别人给予的好意,自己却不具备相应的表达通道。云南拍戏时,一个场工给高仓健打伞,打了三天,高仓健觉得实在不能受——他脱下腕表送给场工,自己去站在阴凉处。而分手之前,张艺谋对张伟平言听计从,义务打工多年,一定意义上,也是他对接受到的情意的回馈。普通人看来,这样的交换绝对可以算是吃亏,但在当事人而言,他们或许只恨,自己未能有更多的可以付出。
在这个角度理解张艺谋对“士为知己者死”的推崇,或许那就是,他所能想到的,恰如其分的体现情感浓烈程度的表达方式。
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他们的同类。陈丹青因张艺谋结识了高仓健,后来他在日本拜访过高仓健。“他仍是笔直地站着,候在门后,脸上的意思,真好似等来什么老朋友。我想想好笑,一面之交,老头子何至于这么高兴呢。但我也高兴的,不为他是高仓健,而是难得就近观察一位伟大而垂老的演员。”
临别时,高仓健也脱下腕表相赠,陈丹青解读:“显然高仓十二分享受袭击般的馈赠;他又显然羡慕着别人的母亲与儿女,以至非要强行送礼才能安顿他的温柔。看来他在银幕上无数义气凛然的片刻,并非演技,而是真心,抑或,漫长的演艺久已进入他的日常,他要在过于孤独的晚岁——就像他老是形单影只的角色那样——时时找寻自己的侠骨柔肠。”
或许,真的是旁人眼里看到的那样,因为孤独。张艺谋在日本和高仓健在酒店见面,看到所有日本人都对高仓健保持敬意,远远的鞠一个躬,随后离开,并不求为他所知。而张艺谋,他的孤独相比高仓健,似乎还更难堪一些,“国师这个说法,就是把他恶意架到一个高位,当靶子才这么叫的。”史航说。
我们采访张艺谋的时候,他正在给《长城》海报签字,要求把金色签字笔换成黑色的,以和深灰色的海报背景相配,“这是美国人喜欢的风格。”他说。
那你自己会怎么设计?“我觉得要加点悬疑,比如伸一个爪子,或者远远的一个眼睛,毕竟是饕餮嘛,现在这样就是一个四平八稳的大片海报,没什么新创意。”
我们问他为什么不提出建议。“没人问我这个事情,我就不说,交给大家就好,做好了大家高兴,做不好也别抱怨。谁让你个儿大呢,人家在你面前都有压力,你一说人家听还是不听,就把人家节奏打乱了。”他顿了一下,又说:”没人问我,我有各种想法,不光是电影,天文地理,各个门类的艺术,你各种事情上跟我谈,我都有想法,还常常是独到的见解,但是,没人跟我谈。”
他跟人们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墙,成因是敬也罢,嫌也罢,都是公众人物的代价。一定意义上,作为一个功成名就的导演,张艺谋至今保持高产、保持“干活儿”的热衷,是因为,这让他不孤独。“我这么一堆老伙伴,不拍电影,有什么理由把大伙儿聚在一起啊。”他曾经这样对史航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