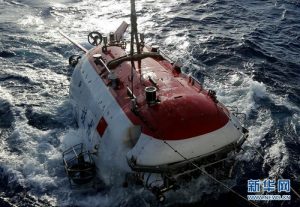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赴美留学的中国“空降孩子”
这是一个怪异的历史时刻: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里的精英,纷纷将其独生子女送往地缘政治对手的学校。
我第一次见到杨金凯(音),是在他登上飞机前往美国两天前。那天,雾霾(专题)笼罩在他的家乡、工业城市沈阳上空,把太阳变成了一团鬼影。这名16岁的少年在他家的公寓里踱来踱去,妈妈则给他的行李箱贴上标签,在里面塞满了舒适家居生活所需的东西:加绒睡衣,筷子,方便面。她指给我看将会留在儿子卧室中的一件孤零零的纪念品:她的独生子的一幅真人大小的绣像,用熠熠生辉的金线绣成。“我一整年都在绣这个,”她说。“我知道这一刻终将到来。”
杨金凯从未出过国。但他已经为了在美国的新生活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科尔宾(Korbin)(“听上去像美国人,对吧?”),对即将到来的冒险之旅充满憧憬。“会是一段神奇的经历,”他说。“我会交很多美国朋友。我想找个美国女友。或许”——他喵了父亲一眼——“我还会弄一把枪。”整个夏天,科尔宾一直通过观看美剧《犯罪心理》(Criminal Minds)学英语,也许刷剧热情有些太高了。
为了帮助科尔宾逃离充满竞争和束缚的中国教育体系,他父亲付给一家教育咨询机构将近4万美元,为他在密歇根州的一所公立高中报上了名。杨家的终极目标是让科尔宾就读于美国的顶级大学,他的新高中名叫牛津(Oxford),为其平添了几分魅力。此牛津与英国的那所大学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底特律北部的一个小镇,但这并不重要。科尔宾说,“我父亲对拿到一张牛津文凭这种事还是很感兴趣的。”

Mark Peterson/Redux,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科尔宾在牛津镇高中的课堂上。
即便是在中美两国关系趋冷、彼此敌视之际,中国学生赴美的大潮依然有增无减。目前约有37万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在美国的高中和大学注册,是十年前的六倍还多。他们的经济影响——商务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的数据显示,他们在2015年为美国经济贡献了114亿美元——已经把教育变成了美国对中国的顶级“出口品”。
这是一个怪异的历史时刻: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里的精英,纷纷将其独生子女,即中国以前的一孩化政策的产物,送进地缘政治对手的学校。然而,中国的统治阶层一心想让子女接受西方的自由教育,几乎将其视为某种护身符。中国的教育以死记硬背为重心,培养出了一些世界上最善于应试的人,但很多中国家庭的担忧与大众印象中的虎爸虎妈的担忧截然不同。他们忧心于激烈的竞争会让他们那备受呵护的子女付出怎样的代价,他们怀疑子女的创造力正在被扼杀。习近平(专题)主席眼下领导着一场在中国学校里清除西方影响的运动,但就连他也允许自己的女儿到哈佛大学(Harvard)读书。根据沈阳的一家研究公司在2016年开展的一项调查,83%的中国有钱人打算把子女送到国外的学校里去。这项调查显示,富豪子女出国留学的平均年龄从2014年的18岁下降到2016年的16岁——这是首次降至读高中的年龄。
2005年,在美国高中注册的中国学生只有641人。到2014年,中国学生的数量达到4万人,十年间增加了60倍——目前几乎占到美国高中国际学生的半数。“家长们意识到,如果想让孩子进入美国的顶级大学,就必须早做打算,”融尚私塾(Shang Learning)创始人雪麑(Nini Suet)说。“人们正寻求拥有他们能够拥有的一切优势。”融尚私塾是总部位于北京的一家精品咨询公司,旨在帮助中国孩子做好迎接美国寄宿学校生活的准备,并帮助申请那些学校,收费2.5万至4万美元不等。
在公开宣称“美国优先”的新一届政府入主白宫之际,这种现象还能持续多久是个未知数。它在中国已经遇到了阻力。经济放缓让家庭储蓄有所下降,货币贬值则让美国教育变得更加昂贵。中国学生的基数也变小了:过去十年间,18至23岁人口的数量下降了将近四分之一。
但迄今为止,中国学生的留学热潮仍未降温,其原因不仅在于中国方面的推动,还在于美国方面的招徕。每一个进入美国学校——不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大学还是高中——的中国富人孩子,都会带来乘数效应,这意味着整个社区都得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购买力的支撑。

Mark Peterson/Redux,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月,科尔宾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宿舍里。
至少希望是如此。现实则没那么简单。极度渴望美国文凭的中国家庭花的钱,有很大一部分流入了那些把它们和极度渴望现金的学校连结起来的中介公司囊中。这种配对产生了不同寻常的结果。《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的一篇文章称,将近60%的高中生最终都去了宗教学校,尽管他们来自世界上最大的无神论国家。(这些以信仰为基础的学校所传递出的关于安全、纪律和道德价值的信息,颇受其家长的认同。)另有一些孩子实际上进入了文凭作坊,他们由此可以获得签证和文凭,但几乎不受大人的监督。
公立高中成了最新的前沿阵地:中国“空降孩子”(人们对该群体的称呼)目前只有不到5%就读于公立学校,但在私立学校学生人数趋于饱和之际,美国的某些学区已经开始依赖他们来充抵预算削减、增加文化多样性。
要论与中国的关系之密切,几乎没有哪个地方能与底特律郊外的密歇根州牛津学区相提并论。2010年,牛津镇寻求建立首条把中国学生引入公立高中的通道。这一通道体现着牛津镇高中“我们以地球为教室”的座右铭,还给该校带来了学费收入。随着外国学生的数量日益增长,其他中西部学校也开始效仿牛津的成功模式。但当北京一家教育公司提议为中国学生建造一栋耗资数百万美元的宿舍楼时,一场社区斗争随之而来。
机缘巧合之下,沈阳的科尔宾一家站在了牛津试验的起点上。他的父母是在时常闹饥荒的农村长大成人的,没受过很好的教育。他父亲杨怀国(音)移居沈阳,在依靠锅炉修理和房地产生意发家前,曾以收废铁为生。但他很担心科尔宾的教育问题,以及中考和高考这两场决定中国学生未来的入学考试所带来的严酷学习压力。他似乎看不到任何出路,直到科尔宾的学校与牛津合作,开办了国际分部。条件很诱人:参与该项目,读完十年级以后,科尔宾便可以在牛津高中读两年书,直至毕业。
他父亲坚称这不仅关乎家族的荣耀或者未来的工作前景。“我一直都没那个机会,但我希望我的儿子能明白,”他说,“世界不只是沈阳,也不只是中国这么大。”

2015年,科尔宾(左)和他的室友在密歇根州牛津镇的寄宿家庭里。
中国“空降孩子”(中):美国梦减退了色彩
初到牛津,看到截然不同于中国东北地区的蓝天,发现竟然没什么摩天大楼,科尔宾颇感震惊。他通过看电视得出的印象是,整个美国都应该是纽约(专题)那样的。除了主街和一些百年老店,牛津(人口为3500人)有的只是砾石坑和马厩,林木覆盖的社区以及一条单排商业街,那里有着当地唯一一家中餐厅。科尔宾的寄宿家庭住的房子位于一个绿荫环绕的巷尾,车道上方安了两个篮筐,后院里放着一张蹦床。一夜之间,科尔宾有了四名长着金发的美国手足,以及一位寄宿妈妈,他直接管后者叫“妈妈”。他的寄宿爸爸曾是汽车业的一名工程师,认为中国是导致成千上万个工作岗位在最近一次经济衰退中流失的罪魁祸首。
科尔宾完全沉浸在美国文化中:美式橄榄球,逛量贩超市,甚至去过一个拥有自己的摇滚乐队的巨型基督教堂。在美国冒险之旅中,他并不是孤身一人。密歇根州已经成为赴美国公立高中求学的中国留学生(专题)极为青睐的目的地,数十名来自沈阳的孩子就住在附近。科尔宾和另外23名学生之所以来到牛津,是因为参与了中国的一个学业项目,该项目的中介机构BCC国际教育集团(BCC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Group)跟牛津高中有合作关系。此外,这里还有总部位于北京的为明教育集团(Weiming Education Group)带来的19名中国孩子。这两帮孩子的交集不太多,在某种程度上因为为明教育集团的学生住在罗彻斯特学院(Rochester College)的一栋宿舍楼里。该学院是一所提供博雅教育的基督教学校,与牛津的车程为半个小时。科尔宾对自己能寄宿在美国人家中感到幸运。
他的美国生活与前辈们的生活天差地别。第一批中国留学生赴美是在文革(专题)结束后——接着是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当时很多人都非常穷,为了生存要去捡易拉罐或者当清洁工。现如今的中国学生一般都比其美国同学,尤其是公立高中里的美国同学富裕得多。在牛津,看到中国孩子炫耀各个版本的新款iPhone(科尔宾只有一部),即便是中产阶级出身的美国学生也会羡慕嫉妒。中国孩子兜里动辄揣着成百上千美元现金,而且通常每天都要换一双名牌运动鞋——耐克(Nike)、彪马(Puma)、阿迪达斯(Adidas)。科尔宾的中国室友奥斯卡·寇(Oscar Kou)喜欢谈论他父亲的多辆豪车,曾花数千美元买了一部功率特别大的笔记本电脑,结果把寄宿家庭房子里的保险丝都给烧断了。
交美国朋友并不像科尔宾想象的那么简单。牛津高中总共有1845名学生,中国学生总是在走廊里围在一起,用普通话交谈。科尔宾渴望和美国同学交流,但每当他试图这样做,谈话都会因为他弄不懂他们的文化指涉或俚语而冷场。不过,科尔宾对自己的任务并不讳言。“我是一个中国男孩,”他告诉班上的同学,“但我非常非常想交美国朋友。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最好的机会或许出现在那年秋天的返校日舞会上。在迪斯科闪光球发出的眩目光线下走来走去的科尔宾鼓起勇气,邀请一个美国女孩共舞。她只是大笑。找另一个女孩,再次被拒。最终,第三次邀请获得了成功——恰逢一首慢歌响起,跳舞的人变换队形,两两相拥。科尔宾停下脚步,手臂垂在身侧。“我完全呆住了,”他说。那个女孩走开了,重新回到朋友们身边,留下科尔宾独自发愣,琢磨着一个中国男孩是否永远也无法在美国找到自己的节奏。
如果你像我一样,和威廉·斯基林(William Skilling)初次见面是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会很容易把他当成一名传教士。那天,斯基林穿着熨得颇为笔挺的卡其布长裤,上身是一件前襟有钮扣的白色衬衫,头上的短发梳得一丝不苟。他要去的是中国内陆一个尘土飞扬的城市。作为牛津社区学校(Oxford Community Schools)的总监,斯基林也的确把自己视为全球化教育的一名传道者。这是他的第十九趟中国之旅,此行的目的是审查为明教育集团在比邻牛津高中的土地上斥资数百万美元建造一栋宿舍楼的计划。“这将是开创先例之举,在任何一所美国公立高中都没有过,”他说。
斯基林曾经是一名教“政府与经济学”的高中教师。对他而言,该宿舍楼项目是花多年时间结交中国官员、教育工作者和商人所取得的成就。他首次涉足中国市场是在2008年,当时他在中国政府帮助下开办的普通话语言项目,后来成了美国学校同类项目中规模最大的之一。现如今,在牛津的学校里,从幼儿园到12年级(K-12),共有2300多名学生每天学习中文。斯基林说,“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我们在美国教育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帮助学生做好在这样的世界上生活和工作的准备。”这些普通话课程也是当地政府旨在吸引中国人到密歇根东南部地区投资的计划的组成部分。“我们这个州没能在中国市场有所斩获是有原因的,”斯基林告诉我。“密歇根把自己的困境归咎于中国,给中国人留下了负面印象。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是给予中国最大的赞美:开办世界级的普通话语言项目。”

在牛津镇高中的毕业典礼上。
北京方面懂得投桃报李。2013年,国家机构汉办——该机构运营着由诸多孔子学院构成的网络,颇具争议的孔子学院以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中国文化和语言并进行宣传为宗旨——授予牛津社区学校“年度孔子课堂”称号。斯基林借助这种认可和20所中国学校签定了姐妹学校协议。过去7年间,牛津至少有40名不同的教师和管理人员造访过中国。其中一项重要协议是和科尔宾在沈阳念的那所公立学校签定的,后者创办了一所国际学校,面向的是像科尔宾这样想去名头响亮的美国高中读书的中国学生。
利用该协议,斯基林为牛津带来了首批中国学生。他还想办法绕开了美国关于国际学生只能在公立高中上一年学的限制性规定。通过请当地一所大学院校在第二年为中国学生的F-1学生签证做担保,斯基林称他们可以继续留在该高中——并继续缴纳学费——只要他们也注册了全日制大学水平的课程,并缴纳了学费。第二年非常重要:中国家长希望孩子有足够的时间为迎接美国大学生活做好准备。斯基林告诉我,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没有立即表示反对。“从来没人这么做过,因此没有规章或者路线图可循,”他说。“这实际上是一块白板。”
很快,牛津就吸引到了怀有更大雄心的中国公司。为明教育集团总裁林浩在2012年末造访密歇根时,勾勒了这样的前景:以美国腹地的实验区为起点,将有1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高中入学。自称中国最大民办基础教育集团之一的为明,在国内遵循着同样的战略,已经在九座城市里打造了15个校园,共有3万余名学生。正如林浩对到访的一位来自俄亥俄州南部乡村的总监所说:“中国有句老话:‘农村包围城市’。”
一年之内,牛津和为明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确保输入更多中国学生——在接下来的20年里,每年都会有多达200名中国留学生涌入。为明每年要为其送来的每一名学生向牛津社区学校支付1万美元。这对一个面临预算压力的学区而言无异于天降甘霖,但远远不能和中国家庭支付给为明的包含学费、食宿费、保险费和英语辅导费在内的4万美元相提并论。(该公司称,为了开拓中国的中产阶级市场,已经把费用降到了3.05万美元。)
为明还向美国公立高中许以了更大的奖赏。该公司承诺,如果中国学生达到一定数量——从80人到100人——它就会斥资数百万美元建造一处学生中心和宿舍,不用学校花一分钱。随着为明送到牛津的学生越来越多,北京和密歇根的建筑设计师开始绘制宿舍楼的蓝图。我于2014年春天在机场见到斯基林不久后,他返回北京,和林浩一起研究拟议中的宿舍楼的蓝图。两人的碰面地点是林浩的办公室,那里的设计有意模仿了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会晤以恢复中美邦交时所在的房间。林浩办公桌后方的墙壁上有多幅古旧地图,每一幅都代表着为明在其境内办了学校的一个省份。或许要不了多久,密歇根的地图就会跻身其中。“林浩和我相互理解,”斯基林告诉我,“因为我们都是有远见的人。”
科尔宾的音乐欣赏课上到一半,牛津高中的喇叭响了起来。“紧急情况!”一个声音宣布。“一名持有武器的闯入者已经进入大楼!”科尔宾的同学们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俯下身,冲向门口。

Mark Peterson/Redux,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科尔宾在学校里。
科尔宾没明白大家为什么乱作一团。他的英语水平有所提高,但词汇量仍然有限,喇叭里的话对于他而言尤具挑战性。他已经习惯了课间播放的摇滚乐,那些音乐所制造的快乐的喧闹绝对无法见容于刻板的中国学校。但这一次,喇叭里的声调非常严肃:“老师们,保证你们教室的安全!”当音乐老师督促所有人进入隔壁的女生洗手间时,科尔宾愈发困惑了。“快点!”她喊道。科尔宾终于跑到了厕所隔间里,老师在他身后锁上了门——他们静默而又兴奋地等在那里,直到演习结束。
后来,科尔宾对这段经历报以大笑。他几乎忘记了,枪支、骚乱、校园枪击(专题),这些母亲对美国生活的恐惧几乎毁掉了他在美国学习的机会。父亲在他开始美国生活之前对该国进行了考察,主要是为了向妻子保证他俩的儿子足够安全。在牛津,科尔宾面临的唯一危险来自他想要赢得美国朋友的无辜行动。
有一天,一群运动员和懒散的学生邀请科尔宾进男厕所抽几口电子烟。这种邀请对一个拘谨的中国孩子来说很不寻常,但他很高兴能成为一群美国人中的一员。“酷小孩从来不学习,”他被告知,到那时为止,科尔宾一直是个认真勤奋的全优学生。在那以后,他放松了学业,开始举重,认为“等我练出点肌肉,”就可以吸引到女朋友。
但当他的新朋友开始逼着科尔宾和他们一起戏弄其他孩子时,他疏远了他们。他不想对着学校仅有的几个非裔美国人学生喊叫种族主义词语,也不想用普通话对其他中国孩子们说骂人话。“我这么努力尝试交美国朋友,但我失去了自己的中国方式和性格,”科尔宾去年告诉我。“我不再那么渴望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我想成为我自己,中国人。
随着他的这部分美国梦失去光泽,科尔宾开始埋头于自己的学业,并勃发出了强烈的爱国心。2015年9月,北京举行了一次布满导弹的军事阅兵,以庆祝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击败,科尔宾当时在社交媒体上贴了一张中国国旗的图片,附以文字“伟大的中国”。在学校,他几乎和一个说中国“独裁”的学生打了起来。他愤怒的对象不是一个美国人,而是和他一样的中国学生。
科尔宾和奥斯卡离开了他们的寄宿家庭,搬到了另外四个中国学生的住处,那里有一位本地的奶奶照顾他们。科尔宾停止了举重练习。他不再想要一个美国女朋友。他几乎不再和美国学生互动,因为在他就读的大学水平班级里(这是他在第二年里保持美国签证的要求)所有人都是中国人。
不过,对于在高年级度过的那一年,科尔宾的记忆还是很美好的。在他重新开始以学业为重后,他的平均绩点上升到3.96分,接近全班第一,并且他的标准化考试分数刚好在他申请大学时有了进步。再次成为书呆子的感觉很好。“我意识到我是独子,是全家人的独苗,”他告诉我。“父母为我付出了很多,我为什么不应该努力学习?”
(明天请继续关注《纽约时报》系列报道《中国“空降孩子”》。)
中国“空降孩子”(下):留在美国
“你是来参加关于中国入侵的会议吗?
当我驶入牛津学校的停车场时,一个留山羊胡、戴棒球帽的汽车技师出现在我车窗前,抱怨着说起当晚公共论坛的主题:为明(Weiming)计划建立自己的牛津高中宿舍。“教育中国孩子真的是我们的责任吗?”他问。
普通话课程,中国学生的涌入——直到2014年10月,这些牛津开始移入中国轨道的迹象几乎没有遇到阻力。但提议中的中国学生宿舍触动了敏感的神经。董事会会议陷入混乱之中。当地报纸《牛津领袖》(Oxford Leader)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与魔鬼做交易》(Making a Deal With the Devil)。现在,这个技师和其他60名居民聚集在学校中庭,斯基林发现自己处于守势。“我是来缓和这个局面的,”他说。
谈过文化交流的好处后,斯基林简述了财政状况。他说,当学校实现了录取200名自付学费的中国学生这一目标后,估计每年将会有130万美元的净收入落进学校腰包。他认为,更大的优惠还要算是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宿舍,包括八间教室,可供所有学生使用。“我们不用支付一分钱,”斯基林说。“这是一种双赢。”
在充满纷争的问答环节快要结束时,斯基林谈到这个项目可以如何把中国的钱带到密歇根州。“你们已经听唐纳德·特朗普(专题)说过,中国正试图利用我们,”他说。“我同意。我们愿意出卖灵魂,只求打入中国,这是个错误。”我背后的一个女人对同伴低声说:“但这不就是他正在做的事吗?”
在这些事件背后,是一群开始研究这项国际计划的牛津公民。这个团队名为“20队”(Team 20),其倡导者是一位马厩主人凯莉·罗斯纳-迈耶斯(Kallie Roesner-Meyers)。“我不认为这个社区反对接受外国学生,”她说,“但是围绕着这个中国计划,有那么多的秘密和错误信息,我们需要了解更多的东西。”2015年春天,“20队”根据《信息自由法》向该地区的相关部门提出了一系列申请,并最终发现,学校董事会已经同意了一个基于斯基林建议的协议,为期20年。
为了回应来自罗斯纳-迈耶斯的信息,联邦特工向斯基林质询了他向为明提供的咨询工作(斯基林说,他在牛津这笔协议完成之前就停止了咨询服务)。其中一个特工还想了解更多关于中国学生停留两年而不是一年的签证操作情况。据斯基林称,这些特工说他们“没有看出任何问题”,他告诉记者,罗斯纳-迈耶斯“需要平静下来”,但压力还在持续。斯基林在当年晚些时候退休,而为明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就搁置了宿舍项目。
为明依然有大约100名学生留在牛津。而在它的中国学校里,有数以千计的学生期望来到美国,寻找旗舰设施位置的工作还在继续。2015年,该公司报价1260万美元,想在康涅狄格州西哈特福德(West Hartford)拍下58英亩房地产,提议将该处的前康涅狄格州大学校址改建为一所能容纳500名学生的国际学校,其中部分学生可以进入该市的公立高中。当地官员支持这一计划,但是去年5月,由于当地人反对让一个罕为人知的中国公司控制该市中心的土地,市议会否决了这一提议。

Mark Peterson/Redux,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科尔宾和室友在寄宿家庭外的球场打球。
为明的牛津宿舍项目的暂停,以及政府对其国际计划的未竟调查,也是西哈特福德市辩论中的考虑因素。到了11月,国土安全部提出了一项裁决。这种签证操作在未来将不被允许,这对牛津开创的模式是一大打击。
牛津没有受到惩罚,但它今后不能在校园里收留中国学生超过一年以上。目前的41名二年级中国学生被允许留下,但现在他们必须全部学习他们的签证赞助机构罗切斯特学院的课程,而不是牛津高中的课程。到6月,经过一个学期的隔离之后,这些孩子甚至可以得到高中毕业证书。一年级学生的未来则悬而未决。明年,他们可能不能从牛津毕业,要重新进入中国的高考体系也已经太迟。所以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可能会回到国际学生的大转盘上拼命争抢,寻找另一所明年可以入学的学校。
去年6月,在牛津高中的毕业典礼上,按照姓氏的字母顺序,“Korbin Yang”的座位被安排在最后几排,周围是一群中国同学,他们的姓氏都以字母X,Y或Z开头。他们仿佛一种学校之中的学校,看着他们几乎不认识的美国毕业生们从眼前走过。许多本地学生在走上讲台时都得到了热烈的掌声。科尔宾的名字——“杨金凯,以极优成绩毕业”——只得到了稀稀拉拉的掌声。秋天,科尔宾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他能进入一所排名前50的大学,令父母非常自豪,那座学校已录取了将近2500名中国学生。
去年夏天我去沈阳看望科尔宾时,他带我去了一家部分由他父亲所有的美国风格精酿啤酒吧。在台球桌边,他对自己在牛津的经历做出了正面评价。不过,他承认,他两年都没有交到一个美国朋友,就这样离开了密歇根州。这让他感到惊讶。“奇怪的是,我认为这种经历让我更加欣赏中国文化,”他说。这是海外中国学生的一种普遍情绪,他们发现自己的外国体验加强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夏天,科尔宾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书籍,接受武术训练。在美国,他找到了自己的中国心。
现在,在宾州大学的第一年已经过了一半,科尔宾可以一整天的时间都不说一句英语。“我身边总是中国的朋友,”他说。“我没有机会认识美国朋友。”当前的政治气候可能只会让他进一步隔离。科尔宾以合法身份留在美国,努力学习,倾向于电气工程专业。但是,一个越来越把他的家乡视为经济和安全威胁的国家会有多么好客?如果特朗普所说的那些严厉对待贸易的话是认真的,那么中国学生虽然不在这样一场战斗的前线,却可以成为一个双方都很容易拉动的杠杆。限制签证的附带损害将是破坏性的,不仅对学生本身,而且对高中和大学也是如此,特别是对于中西部地区,那里已经依赖于每年来自中国的数十亿美元的经济贡献。
更大的威胁可能来自中国内部。去年年底,习主席反对外国势力的意识形态运动瞄准了那些为科尔宾赴美做准备的学校。这种打压将如何影响中国留学生流向海外,目前还不清楚。父母可能被迫在孩子年纪更小的时候就把他们送到国外,以此逃离关闭的闸门。
对于科尔宾来说,虽然缺少美国朋友,民族认同感也被重新唤起,但是美国高中仍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去年圣诞节,考试结束后,他没有回沈阳,而是回到了牛津。他的第二个寄宿母亲送了他两件连帽衫和一些他最喜欢的巧克力,并且做了一顿圣诞大餐。科尔宾则送了她一个马克杯,还跟几只他曾经从小帮忙照顾的狗一起玩。“我真希望自己还在那儿,”他告诉我,听起来只像是一个普通的大一新生在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