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2011年,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彭博新闻社的创办者,纽约(专题)市前市长,个人财富高达475亿美元)向塞拉俱乐部(the Sierra Club)捐赠5000万美元,是塞拉俱乐部史上接受的最大一笔捐款。这笔捐款计划被用于扩大该组织的“超越煤炭运动”(Beyond Coal initiative),该运动旨在关闭美国境内的燃煤火力发电厂。2015年,他的捐赠额超过3000万美元。塞拉俱乐部宣称“超越煤炭运动”迄今已经推动251家燃煤火力发电厂关停,布隆伯格的捐赠对此起到了很大作用。
如果你是一个想要推动可再生能源替代煤炭的环保主义者的话,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如果你是一个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生计被夺走的煤矿工人,这就未必是什么好事了。在民主社会里,双方也许会在立法者面前争论是否要关闭燃煤发电厂,也可能用选票表达意见。但是,布隆伯格总额8000万美元的捐赠毫无疑问将给环保人士增加巨大的砝码,进而有力地推动变革成为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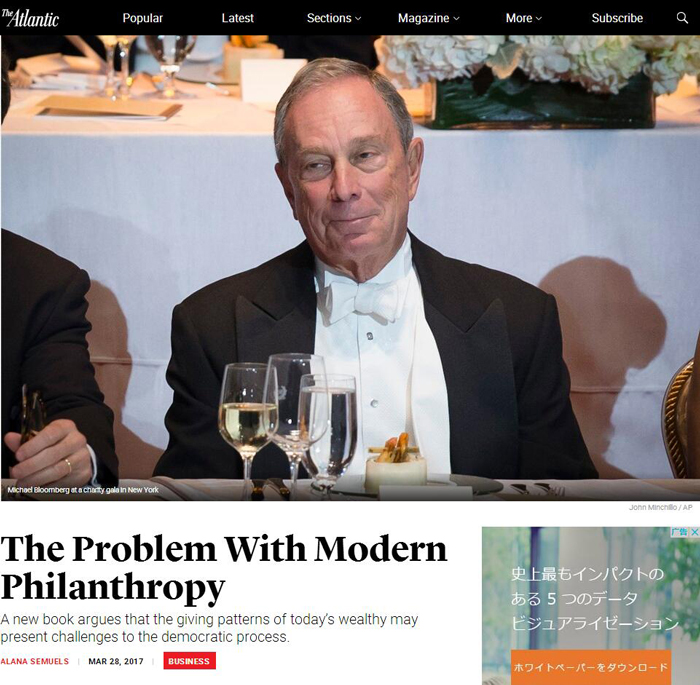
在今天这个美国财富极端聚集的时代里,布隆伯格捐赠巨款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科技和金融“造富运动”所成就的富豪们都发誓要进行规模空前的捐赠。“但是这些捐赠却对民主社会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慈善内幕网站(Inside Philanthropy)的创始人和编辑戴维·卡拉翰(David Callahan)在他的新书《捐赠者:新镀金时代的金钱、权力和慈善》(The Givers:Money,Power,and Philanthropy in a New Gilded Age)中写道。
这些捐赠都在政府职能收缩的时候出现,有时慈善资金成为了政府职能的补充或替代品。这意味着捐赠者能够决定研究什么问题、邀请哪些学派以及哪些议案可以付诸投票表决等等。“在政府削减开支的时候,能有这些新的捐赠当然是好事情”,戴维·卡拉翰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但是换个角度来看,金钱毫无疑问也意味着权力和影响力。”
长期以来,捐赠者们都会就政府不久后可能采纳的新模式进行试验,例如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the 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为今天的911应急电话系统搭建了雏形。
卡拉翰说,过去的基金会通常细水长流地使用已经过世的捐赠者的财富,通常会在一些政策领域进行审慎的尝试。而如今捐赠者们大多都还在世,他们非常关注自己的钱花在了哪里。他们想要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快速的变革,而且通常他们对变革的目标也有很明确的想法。他们中很多人都希望能对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或国家的政策进行改革。
作为一家慈善新闻网站的创始人和编辑,卡拉翰十分熟悉那些仍然在世的捐赠者和他们花钱的方式,他的新书中到处都是违反民主精神的慈善家们的例子。巴里·迪勒和黛安·冯夫丝汀宝夫妇曾提议在哈德逊河上建设一个新的岛屿公园,并提供了公园建设的大笔资金,而且并没有在当地筹资的计划,他在书中写道。
慈善家戴维·韦尔奇对非营利机构“学生为重”(Students Matter)提供资助,该组织支持了范盖拉(Vergara)对加利福尼亚州的诉讼,该诉讼旨在摆脱加利福尼亚州法律对辞退基础教育终身教职教师的限制。
沃尔顿家庭基金会与布罗德基金会等组织进行了合作,试图让洛杉矶(专题)半数以上的学龄儿童进入特许学校就读。
每一项议案都有其反对者,但是他们在决策中的影响力远不及捐赠者们,有时他们甚至被完全排除在民主决策过程之外。“私人捐赠者无需对任何人负责,而民选官员理论上要对我们所有人负责。但是,未来我们或将进入一个私人捐赠者的影响力比民选官员更大的时代”,卡拉翰写道。
学术圈内长期以来都在辩论基金会在民主社会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去年出版的《民主社会的慈善事业》(Philanthropy in Democratic Societies)一书中收录了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亚伦·霍瓦兹和瓦尔特·朴尔合写的一篇文章,他们在文中提出作为慈善事业新形式之一的“破坏性慈善”可能是有害的。它们将“破坏性慈善”定义为与政府争相提供服务,而不与政府进行合作,霍瓦兹在一通电话中这么告诉我。
这种慈善的麻烦之处在于它会重塑大众的议程。“破坏性慈善希望以出资人的意愿重塑民众的价值观,试图影响和改变民意和需求,而非虚心听取民众的意见”,霍瓦兹和朴尔写道。特许学校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们通常与公立学校的系统形成竞争,并最终取而代之。这些捐赠通常都很少听取公众意见,却对公共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
其实,围绕慈善家们是否挑战了民主的争论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斯坦福大学的罗布·赖克(此人与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同名)去年在美国政治学会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说,早在1912年约翰·洛克菲勒首次进入国会,想要获得一张设立基金会的联邦许可时,他就曾受到来自政府官员的抵制,官员们质疑洛克菲勒的慈善动机。当时美国公民自由协会曾经在听证会上质疑洛克菲勒基金会是否“与民主社会的整体观念相冲突”。
卡拉翰并不知道自己站在辩论的哪一边。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们很难去反对为阻止疟疾传播提供资助的人,也很难去反对在去世前将财产悉数捐出的人。但是“慈善家们比过去更为激进”这个论点很有说服力,这也是现在引发关注的问题。
慈善家们也推动了美国传统基金会和美国进步中心等智库机构的诞生,他们公开支持某种政策倾向的研究。例如《纽约客》杂志的记者珍·迈尔最近撰写了一篇关于罗伯特·默瑟的文章,此文称默瑟的基金会资助了许多攻击希拉里·克林顿的非营利机构和智库,而希拉里·克林顿最后在美国总统竞选中铩羽而归。
慈善家们也改变了包括塔尔萨和洛杉矶等城市的格局,建设了由他们维护、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公园和博物馆。他们捐资数千万美元支持洛杉矶特许学校的扩张,希望在未来十年内半数以上的适龄学童在特许学校就读。
卡拉翰表示,他撰写《捐赠者》一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让人们认识到当今的慈善家们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力。“我认为只有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富豪们在借助慈善行为获得极大的权力,人们才更有可能认识到慈善活动就是有钱人发声的工具,而普通人则只能在嘈杂里挣扎”,他对我说。
如何遏制富有的捐赠者在公民社会中日益增长的权力?卡拉翰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改变慈善机构的纳税地位(tax status)就是其中一种方案。毕竟,一些慈善家们利用慈善团体来推动公共政策的变革,但是他们收到的捐赠并未被征税。
例如,威斯康辛州的一个风险投资家所运营的艾因霍恩家庭基金会出资在少数族裔聚居区内设立公告牌:“选举欺诈是严重犯罪行为”,提醒人们选举欺诈最高可判处三年监禁。这些公告牌设立的位置表明它们具有很强的党派属性,但是艾因霍恩家庭基金会却能够享受税收减免待遇,卡拉翰写道。其实这些慈善税收减免最终还是由民众来买单,预计未来10年内这项开支高达7400亿美元。
许多由基金会设立的关注公共政策议题的机构都依照美国税法501(c)3条款设立,对这些组织的捐赠可以享受税收减免,而按照501(c)4条款设立的机构所获的捐赠则不能享受税收减免待遇,这些机构的目标是影响立法和公众。但是许多按照501(c)3条款设立的机构仍然在为影响公众而努力,例如它们撰写报告支持或反对最低工资的相关规定。
卡拉翰认为,美国国内税务局应当缩窄对501(c)3条款中慈善活动的定义,如果对这些组织捐赠的款项具有党派性质的用途,那么就不能享受税前扣除,这样纳税人也就不再为慈善家们的公共政策运作买单。
卡拉翰还要求基金会提高可信度,让普通民众也可以知晓慈善资金何时被用于影响公共政策和他们的生活。推动公共政策变革的非营利机构可以在不披露捐款人的情况下这么做,卡拉翰写道。他认为基金会应当就善款的流向披露更为详细的信息,美国国内税务局应当支持下属税务稽核机关的工作。尽管这些工作可能会产生成本,但是这可以用基金会缴纳的每年2%的投资收益税支付,目前这笔钱还没有派上这个用场。
卡拉翰还建议就慈善事务设立新的办公室,以便监督慈善机构遵章守纪。
当然,在许多美国人不相信政府的这个时代,这些政策也许很难获得市场。这也就是将改变的重任交给慈善家们自己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的原因。在《捐赠者》一书中,卡拉翰收集了一些组织的案例,它们希望从社区中获得反馈,而非颠覆这些社区。
例如芝加哥(专题)社区信托基金会(the Chicago Community Trust)邀请芝加哥大区的居民前来讨论他们眼中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再告诉他们该基金会当前的工作重心是什么。波士顿(专题)的一些受助人(低收入的女性)也运营着一家基金会,该基金会由一位名叫卡伦·皮特曼的女性所创立。但是眼下这样的例子还很少,离我们也很远。
慈善家们可能不会留意到卡勒汉的建议,有那么多钱可以分配的好处之一在于可以随心所欲,不用听取任何人的意见。但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隔阂如果越来越大,一些明智的慈善家们可能会逐渐明白:有钱不仅仅意味着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且也决定着别人的生活中会发生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