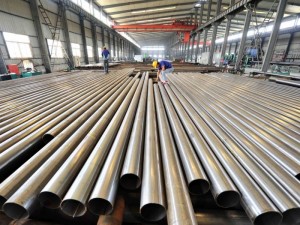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近日,改编自作家陈忠实同名小说的电视剧《白鹿原(电视剧)》虽然收视率如不预期,但也引发了一些话题,剧中出现的“陕西油泼面”、白鹿村口的“傻子”也成为新晋“网红”。
《白鹿原》刻画了白鹿村人在时代变迁下的颠沛流离,在精神的“乌托邦”和残酷的生存现实交织相荡中,“仁义白鹿村”所承载的儒家传统文化从未消失。伴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观众也展开了对“乡土作家”陈忠实、路遥、贾平凹及其经典作品的对比。许多观众认为,与《平凡的世界》和《秦腔》相比,《白鹿原》拥有更加宏大的格局,更加深刻地刻画了时代更迭下的人性群像,再加上小说中所体现出的儒家传统文化,整体显得更加厚重。

电视剧《白鹿原》剧照
众所周知,《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和《秦腔》都是现实主义的乡土题材小说,都曾获得过茅盾文学奖,在乡土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此,笔者无意对三者作出孰高孰低的评价,仅试图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说一说三者的不同风格。
不同的地域文化造就不同的创作风格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作家的文学创作都是从他们的故乡生活开始的,甚至故乡将伴随他们的整个创作生涯,成为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记。譬如鲁迅笔下的绍兴,萧红笔下的呼兰河,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不难发现,不同的地理环境往往产生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的地域文化也会对文学作品的风格产生影响。陕西籍作家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也许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样的影响。

路遥
从自然条件方面讲,陕西省可以被分为三大地域:陕北、关中和陕南。陕北位于黄土高原与蒙古草原的交界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融,使这里的文化带有一种野性。关中以西咸地区为中心,宋代道学中主流之一的“关学”正是在此发展起来,并且在历朝历代的更迭中逐渐占据了关中地区的主流文化形态。陕南地处秦岭与巴山之间,地势崎岖,相对比较封闭,使这里保持着质朴自然的生存形态。
三大地域自然条件的分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人文特征,造成了各自地域文化的巨大差异。陕北以路遥为代表,关中以陈忠实为代表,陕南则以贾平凹为代表。三位作家虽然都出身农家,深谙乡村人民生存的艰难和精神的困境,但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他们的作品还是体现出了不同的风格。
耕读传家的仁义白鹿原
八百里秦川,北接黄土高原,南临秦岭,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之成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以“关学”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慢慢在关中这片历史悠远的土地上生长、绽放,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关中人。陈忠实就是在这片充满“仁义”的热土上成长起来的,并将儒家的传统观念贯穿至整部《白鹿原》。
《白鹿原》的主人公白嘉轩始终秉持儒家“仁义至上”的人伦标准,用“仁者爱人”的道德准则规范自己,用“耕读传家”、“学好为人”的传统精神教育下一代。从白嘉轩的父亲秉德老汉给长工鹿三寻媳妇,白嘉轩与鹿三以兄弟相称,送鹿三的儿子黑娃上学,到饥荒瘟疫中,仍坚持留下鹿三,甚至与鹿三同睡在马号里,同喝一瓶西凤酒,白嘉轩可谓是“仁至义尽”。白嘉轩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但他信仰的却是“仁义至上”的儒家信念。这种信念并不是通过背诵四书五经得来的,而是通过各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沉淀在了他的血液中。

《白鹿原》
白嘉轩的姐夫朱先生则是一个传统儒家精神的“卫道士”,被白鹿原人称为“圣人”。他清高儒雅,无所不知,“处江湖之远”却又不忘黎民。在小说中,朱先生通过制定“乡约”,将儒家的道德理念落实为具体的行为准则,使村民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着儒家文化的耳濡目染。在得知妹夫白嘉轩种植罂粟时,他毅然耕毁大片的罂粟幼苗,恢复往日的躬耕传统。国民革命时,他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劝退巡抚的20万大军,使百姓免遭战争的迫害。灾荒饥饿之年,他亲自指挥赈灾队,与乡民同甘共苦。日寇入侵,他投笔从戎,誓死抗争。总而言之,朱先生将传统儒者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的双重品质表现的淋漓尽致。
此外,黑娃、白孝文的反叛与回归家族,同样寓意着对儒家传统家族观念的回归。我们可以说《白鹿原》上的一切都被打上了儒家的印记,甚至儒家文化中一些迂腐的观念也被表现的入木三分。
平凡的世界,黄土地上的抗争
路遥是陕西榆林人,在《平凡的世界》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一句看似简单的话,倾注着路遥对于陕北黄土地的无限心血和热爱,同时路遥也将“黄土地”贯穿到了整部作品中。
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采用了大量的“黄土地”方言,例如用“圪崂”、“山峁峁”、“塄坎”等来形容黄土地的地貌;用“门楼”、“硷畔”来反映黄土地的村舍;用“脚地”、“灶火”来描述黄土高原上窑洞的特征。

《平凡的世界》
除此之外,路遥还多次运用了黄土地特有的信天游来抒发人物的感情。当润叶局促不安地从城里跑到双水村地头,找找她心心念念的少安哥时,对面的山上忽然飘来一个庄稼汉悠扬的信天游: “说下个日子呀你来不来,硷畔上跑烂我的一双鞋。墙头上骑马呀还嫌低,面对面坐下还想你。山丹丹花儿背洼洼开,有什么心事慢慢价来。”陕北信天游的运用,不仅恰如其分的将小说中人物含蓄羞涩的感情表现出来,更暗含着路遥对陕北黄土地文化深沉的爱。
黄土高原自古以来就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争夺的要地,饱经了沧桑与苦难。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人们,自然会在苦难中养成倔强刚毅的品质。路遥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也是凭借着这股刚毅不服输的精神,在严酷的环境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在上学时经历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身体折磨,与同学郝红梅的朦胧感情也最终幻灭,他并没有因此停止对于苦难的抗争。即使到了建筑工地上,孙少平依然“趴在麦桔杆上的一堆破烂被褥里,在一粒豆大的烛光下聚精会神的看书,那件肮脏的红线衣一直卷到肩头,暴露出令人触目惊心的脊背一一青紫黑淀,伤痕累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使孙少平悟出了自己的苦难哲学:“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通过这一段血火般的洗礼,他相信,自己历经千辛万苦而酿造出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直至最后恋人田晓霞的死带来的沉痛打击,孙少平依然能够挺起胸膛坦然面对,此时的他已经超越了苦难。
明代文学家陈继儒在《侠林序》中讲道:“贫贱非侠不振,患难非侠不脱,辟斗非侠不解,怨非侠不报,恩非侠不酬,冤非侠不伸,情非侠不合,祸乱非侠不克。”孙少平在苦难的境遇下,用拳头给予对少女图谋不轨的包工头以最严厉的惩罚;矿井崩塌的危难之际,不顾自己的安危拯救工友。他身上所体现出的这种勇于抗争、匡扶正义、舍身为人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与陈继儒所说“侠”之精神不谋而合。
秦腔里的乡村变化
贾平凹是陕南商洛人,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商洛的乡村呈现出一种小国寡民式的宁静祥和的生存状态。贾平凹曾说:“她(商州)的美丽和神秘,可以说在我三十年来所走的任何地方里,是称得上‘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赞誉。”凭借着对故乡的热爱,商洛的自然风光总是被贾平凹描写得如诗如画,树木、花草、白云、流水似乎都有了灵性。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往往也是温顺、善良、热情好客的,他们保持着本真的生存状态,过着世外桃源一般的生活。然而,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对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秦腔》
小说《秦腔》以一个“疯子”引生的视角展开叙述,他利用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行走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用与众不同的视角观察着清风街所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他看到现代文明把新鲜的事物传播到农村,打破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疯言疯语地说道:“我要儿子、孙子干啥,生了儿子孙子还不是在农村,咱活得苦苦的,让儿子孙子也受苦呀?与其生儿得孙不如栽棵树,树活得倒自在。”这句看似疯癫的话,实际上却折射出了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的远去,新的观念使农村产生了新的生命意识。
贾平凹借引生这个人物,静观当今乡村的变化,面对着农民与土地联系的割断,面对着村民和农村存在的陌生感,面对着正在消逝的农耕乡村,其中既有对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捍卫,也有面对现实的无可奈何。“疯子”的形象被塑造成现代乡村的守望者,表达了贾平凹对传统乡村生活的怀念与追忆。
实际上贾平凹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家乡商州为表现对象的乡土小说,如《天狗》、《商州》;另一类则是以现代都市为背景的“都市小说”,如《废都》、《白夜》等。乡土小说自然流露出贾平凹浓郁的乡土情结,而所谓的“都市小说”通过描写现代文明对田园牧歌生活的巨大冲击,表现的是对城市文明的排斥与批判,对理想中自然无为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向往。
通过对三部作品的地域文化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三者虽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展开叙述,但是受各自文化地域的影响,呈现出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白鹿原》像关中的土地,沧桑浑厚,承载着深厚的儒学文化;《秦腔》像陕南的水,清澈恬淡,有一种“自然无为”的倾向;《平凡的世界》则像陕北的风,带有一种野性的力量,刚毅不屈,有“侠”的某些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