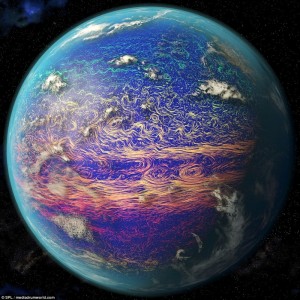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三个男人的马背求生之旅
2008年9月的一天,我正和我的朋友Ben Masters一块儿吃晚饭。那个时候,我们还都是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的学生,在一个马球俱乐部彼此相识,其实那会儿,我们根本还不认识对方,但我们对马和户外运动都情有独钟,而且都想把学业搁置一段时间。正在等着服务生送来fajita(一种墨西哥食物)的空当,Ben调侃地说,为什么我们不试试骑马穿越美国呢?我当即就同意了他这个好主意,而我们人生中的第一次探险旅程就这样诞生了。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Ben经常埋头研究地图,最后终于围绕凶险的落基山脉找到了一条可行的路。3200多公里不间断的跋涉,全无庇护所、休息处和兽医治疗的保障,让我们此行成为近年来颇具挑战和难度的征程,所以我得找到完全可以胜任这项任务的马。我最终寻觅到了两匹野马、一匹阿帕奇矮马和三匹夸特马,这六匹马从未生过什么病,没有在马厩生活过,在冬天都是靠自己觅食,甚至脚上的蹄铁都不完整。

2010年5月,由一句调侃决定的一次从美国新墨西哥州前往加拿大边境的远征正式启程了,此行共三个人、六匹马。第三位加入我们的是Mike Pinckney,他刚刚从科罗拉多大学毕业,是Ben一直以来打猎的玩伴。5月16日,Ben和Mike抵达了美国新墨西哥州的Watrous牧场,我们仨在这儿花了几天的时间调教了一下选择的马匹,当我们认为人和马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就在同月22日从新墨西哥州北部的Canjilon出发了。
刚开始深入科罗拉多州的几周里,我们经历了各种小坎坷和小胜利。然而,我们险些在中部地区的Collegiate山峰的时候就早早结束了这次冒险旅程。Collegiate 山峰是美国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我们选择的那条路线还没有被命名,海拔在3800米左右。在朝南方向路面的行进过程中,一切还算顺利,马匹精力充沛,天气一直都挺晴朗;但是当我们离山顶还有15米的时候却因为坡度太陡而没有办法继续前行。
于是,我们三人决定下马,鼓励它们先行翻越了这狭窄的山峰。这个胜利的喜悦却仅仅维持了一小会儿,因为当我们自己也翻越过来的时候,发现马都被困在了 1.5米深的雪地里。我们赶紧来到它们身边,但是又立刻意识到:能把它们解救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用双手为它们挖出一条生命通道。
分完工以后,我们轮流做着解救的工作:一个人负责寻找下一步可行的路线,一个人负责用双手在冰冷的雪地里挖出一条路,一个人负责牵住马匹并保护它们。四个小时的奋战,我们终于成功地把马带到了一个海拔3048米的地方,一个可以让它们当晚安稳地休息的地方。但我们还是需要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带它们打圈热身,与其说是给它们做热身,不如说是想办法让自个也暖和起来。其实,我们一直在担心马匹的健康状况,之前我们没想到在海拔3600多米的地方会踏破冰层,陷入溪流,湿透的全身感到冰冷刺骨,而且我们都没能生起火来,情况变得更糟糕了。
在穿越黄石国家公园的时候我们遇到了第二个灾难。8月中旬,我们跋涉到了位于美国怀俄明州的拉马尔山谷。到了入口的时候却意外得知山谷在这个季节已经禁止攀爬和野营了,这对我们的行程影响比较大,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要绕道1万6千多米,而改变计划我们就不可能赶在冬天下雪之前完成这次荒野之旅了。于是,我们又打开了地图,最后决心只用一天的时间穿越这个山谷,我这里说的一天指的是不间断的24小时。在进入山谷之前,我们利用白天的剩余时间让马彻底休息了一下,为接下来马拉松式的征程积攒能量。
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走进了拉马尔山谷,眼前的景象让我们立刻就领略了其独特之处:成群结队的北美野牛让我们既震撼又兴奋。如果说以前我们对野牛毫无概念,即便有所认识也只是在《寂寞之鸽》(Lonesome Dove)这部电影里见过Robert Duvall追逐着它们奔跑。想当然地,我们也追赶着它们玩儿,你可能也猜到了,我们立刻就为自己的天真行为追悔莫及。先开始被我们追赶的20多只小野牛倒是被迫撤退了,但是它们跑回了自己的族群,那里有正处于繁殖季节的1000多只极易愤怒的成年公牛和母牛。我们还没来得及转身,就看见200多只庞然大物朝我们跑了过来,又60多只平均体重在900多公斤左右的成年公牛紧随其后,看它们的架势,是不追上我们不罢休了!

如果说我们以前对北美野牛一无所知,相信这会是我们上得最生动的一课了,在相同时段里,它们可以比马多跑出46米!我们立刻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就算我们现在跑回到马那儿,翻身上了马,成为疯狂野牛的盘中之物恐怕已成定局。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逃命要紧。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这里俨然就是一个疯狂的战场,弓背跃起的战马、杀气腾腾的的牛角、让老练的水手都觉得震惊的谩骂,最终,我们还是成功地逃到了黄石河的对岸,就像是躲进了安全港湾。等我们过了河,天色已经很暗了,即使河水把我们和野牛阻隔了400多米,我们依然能听到河对岸山脊之上发出的阵阵低吼声。
我们三人暂时是把心放在了肚子里,给马卸了鞍,自己也把睡袋拿出来枕在头下,席地而卧。就在此刻,我们听到了不可思议的动静——水花四溅的声响。天啊!这群野牛竟然在漆黑的夜里,趟着冰冷的河水直冲我们而来。按理说,搁在平常给马上个鞍根本不算难事,但是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刚刚被一大群野牛追击、现在又耳闻着袭击者愤怒嘶吼的几匹惊恐不安的马,再加上摸着黑给它们备鞍,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
手忙脚乱了相当长的时间,马鞍终于是备好了,逃跑再次开始。这次,我们打算直接沿主路南下,希望可以把那群野牛远远甩开。没想到,我们又错了。拉马尔山谷的一个公园管理员发现了我们,他把车停下来,同我们说了说这里的情况,我们仨才意识到刚刚陷入了多么危险的境地:原来,野公牛到了发情期就会性情大变,从温顺、迟钝变得凶残无比。据说,它们会攻击任何所见到的比自身弱小的生物。管理员还透露,现在山谷暂闭就是因为,每当夜幕降临,从山谷的北面就会冲下一群野牛,和南边的牛群展开激战。而我们刚刚就是处在这两拨阵营的中间地带,方才被3000多只正伺机打上一架的野牛包围着却浑然不知,想想都后怕。而身处的安全区域每一秒都在缩小,管理员建议我们先把马留在这儿,上车跟他离开这里,明天一早再过来找马。
我从没动过这种念头:自己逃生,把马丢在这儿,让它们自生自灭?根本不可能!于是就赶紧寻问其它办法。他建议我们去西侧的Slough Creek,从那儿我们就能出山谷了。他刚从那边过来,虽然没有野牛,却有三只成年灰熊。可那似乎是我们目前唯一的选择,只得硬着头皮上了。
拿上枪,我们就朝着Slough Creek的方向出发。还差90米就到了,可马匹突然受到了惊吓,我们也随即听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一大群恼怒的北美野牛正朝我们快速逼近。管理员提醒不要使用任何灯光,这只能吸引动物的注意,因此我们就强忍着一探究竟的本能硬是把灯光给熄灭了。但在一瞬间,我还是看到了前方450多米远的地方潜伏着几十双愤怒凶狠的眼睛。这群野牛,今晚并没有在保卫各自的族群,事实上,我们已经成了它们狩猎的对象。
于是,我们赶紧给驮货的马卸了行李,松了缰绳,希望它们能跟上领头的马,在万一再遭到袭击的时候为我们争取时间施巧计策,化险为夷。幸运的是,它们的表现和我们设想的完全一样。一路向南,我们逃离了这群侩子手的视线,在随后发现的一块巨石组成的峡谷里面过了夜,载行李的马跟着我们到了这里,开始低头吃点草了。

我们无法确定是否彻底逃过了这一劫。我和Ben牵着坐骑准备随时行动,Mike爬上了距离我俩180多米的一棵树,他带着电灯和信号枪,为的是能第一时间通告我俩牛群的具体位置,好让我们及时骑着马转移阵地。大约过了20分钟,马突然不再吃草了,却像我和Ben靠拢过来,耳朵朝向我们脚下的地面似乎在努力听着什么。很快,不远处就传来了野牛群粗鲁的喘息声和一路过来踩踏植被的声响。
我和Ben一直用耳朵捕捉着能预示袭击的任何动静。几个小时过去了,马竟然也可以同人一样保持安静,没有抓地、没有惊恐的嘶叫。我俩和Mike暂时失去了联络,希望他一直保持着清醒。我们确定听到过野牛近在咫尺的声音,但事后证明是出于精神高度紧张产生了幻听。最后,灰蒙蒙的天际终于照进了破晓的光芒,夜晚的星光逐渐褪去。正当我们暗自庆幸的时候,身后一千米开外的几声狼嚎又将我们拉回了现实。
虎口脱险,熬过了这个夜晚之后,带着对野牛的敬畏,我们北上继续这次征程。感谢太阳照常升起,更深深地感谢我们的动物战友对危险敏锐的洞察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这是我们此次旅程中最为惊险的部分。即便是之后偶尔在远处看到的灰熊都显得相形见绌了。依照原计划,我们按时走出了拉马尔山谷,确保了在隆冬来临之前结束旅行。尽管确实要在最后穿越蒙大拿州的几周时间里克服冰雪带来的困扰,但是我们成功地赶在加拿大进入深冬之前抵达到那里。

感谢我们不可思议的坐骑、以及在沿途中向我们伸出援手的人们,我们三人完成了一场终身难忘的旅程。整个旅途中,很多热心的人们尽可能地给予我们雪中送炭般的帮助,它可以是一杯温暖的咖啡,亦可以是欢迎三个陌生的青年和六匹马走进他们生活的热情和激励。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三个人——他们是Fossil Ridge的导游服务人员Josh Matheny、711牧场的Deb Rudibaugh和蒙大拿州利文斯顿的Phil Nickels。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心人,无论我们是怎样相识的,他们永远是我们此行最幸运的收获之一。
这次探险仅由我们三个人共同完成,它考验的是团队精神以及各司其职的能力。就像世界上其他优秀团队一样,当某一名队员没能被委派做自己擅长工作的时候,这就需要另一名更适合的队员挺身而出——我很骄傲,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一支团队。旅途中,我们认识了很多人,和他们聊了许多,年轻人简直难以相信我们拿生命开玩笑似的冒险,而长辈们则为依然有人在做这类的事情而感到兴奋和欣慰。